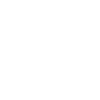SM不是性心理變態,也不是性虐待 - 卡維波(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本文作者: 卡維波(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不论是大众媒体或一般人的观念里,对于SM经常有错误的认识,例如将SM称为「性变态」或「性虐待」,或视为「心理病态」,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说法,这些错误说法也显示这个社会缺乏性权利的意识。
把SM视为性变态乃源自西方基督教的传统,随着殖民主义与性学发展而扩散到非西方世界。基督教认为性的目的就是生殖,凡不是为了生殖的性行为都是不自然的,故而手淫、爱抚、口交、同性恋都是道德上的过错。反对这个宗教传统说法的早期性科学虽然一方面认为非生殖模式的性与道德无关,另方面却同时将
SM这些非生殖的性称为「性变态」,当作某种生理或心理异常。
在现代国家人口节育政策与避孕科技的发展之下,生殖不再是性的唯一目的,性更是为了愉悦与快感,生殖模式的性道德遂逐渐被废弃,手淫不再被教育家与父母视为大敌,肛交也在很多国家被除罪化。更有什者,如果在性活动中追求愉悦快感是自然的,那么SM这些促进性兴奋的非生殖性活动根本就是性常态,是一种性偏好或口味癖好,如同各种助兴的性体位与情趣用品,更无涉道德人格。
很多人以为SM只是少数人的「特殊」性癖好,其实它一点也不特殊,反而是非常普遍常见的,只是很多从事SM的人不自觉而已。例如许多人会在性活动中包含各种形式和程度的抓咬捏捶或其他形式的激烈性爱,更多的人则使用角色扮演,用不同的配件装置器具来营造气氛。最常见的SM除了动作激烈狂暴外,还有口头暴力,例如在性行为中使用禁忌的语言、脏话或者以语言自贬或贬低对方等等。除了这些几乎人人均从事的SM「入门」外,SM还可以被进一步开发而达到更为繁复与仪式化的形式,媒体中常见的皮衣颈扣及捆绑等就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例子。
SM的普遍性有其心理基础。弗洛依德认为在性压抑社会中,人们对于性有羞耻、嫌恶、痛苦、恐惧等心理,这些心理阻碍了性愉悦。可是「性变态」(亦即,非生殖的性,包括手淫、裸体、爱抚等)却有促进性愉悦的功能。
例如,原本裸露是让人羞耻的,但是人们在性交时喜欢脱光衣服,就将羞耻转化为性兴奋。同样的,喜欢口交的人可以把对性器官的嫌恶感转化为愉悦;喜欢SM的人则把原本连结到痛苦、恐惧、无助等心理的性活动转变成快感。这是一种很合理的心理机制。
弗洛依德认为性变态克服了性压抑,因此反而不会因为性压抑而形成精神官能症。易言之,SM把侵犯与破坏的心理以仪式性的行为操演出来,反而比较不会有精神疾病。有心理医生说如果性活动过度依赖SM则是「病态」,这其实仍是预设了生殖模式为性活动的典范。但是热爱SM的人,就像性活动中热爱口交或裸露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心理问题或不妥。
照这样说来,SM不应与性虐待混为一谈。性虐待(sexual abuse)是枉顾对方意愿而施行的身体侵害,SM却是在双方同意之下充分协商而进行的戏码。台湾许多性研究者将SM称为「愉虐恋」是很有道理的,「愉」就是以对方的愉悦为主要关注,「虐」则是双方在一定的仪式程序中建立起互动的角色和戏码。绝大多数的人多多少少都会玩一些愉虐的活动助兴,有许多人只有在某种清楚明显的权力支配之下,感觉到自身的全然无助,才能放松自我的僵化而得到快感。
事实上,愉虐恋正是在这个充斥各种不平等关系的社会环境中模仿或谐拟(parody)暴力及支配,并在协商过程中建立双方的信任感与亲密感,这和真实的暴力与支配大不相同。有些女性主义认为SM展现了男女不平等或男性暴力,这是对愉虐恋的误解,因为异性恋的SM并不一定男支配女顺服,而且在SM中真正主导整个过程的人常常是那个看来被支配的人。 SM中的复杂操作和互动模式还有待我们不带成见的认识。
台湾解严后,性开放的程度虽然很高,但是被称为性变态的弱势「性少数」族群却没有性权的保障,结果这些性少数经常成为被媒体偷窥、被商业剥削的对象,也承受着道德的污名与曝光后的迫害。很显然的,性开放不等于性少数的解放(性解放)。面对这种不符合社会正义的性压迫,除了对社会大众进行更多的性权教育外,台湾的愉虐恋者也应会和同性恋者一样组织起来,争取其不被污名与歧视的权利。
原载于:2002年1月7日台湾《中国时报》时论广场。并收录于《性政治》,游静编,香港:天地图书,2006。页242-245。
这篇文章的写作脉络是:2002新年期间爆发了台湾立法委员黄显洲在五星级大饭店遭强盗疑案,涉嫌女子詹惠华的弟弟詹富顺向检警供称,黄显洲喜欢玩多人的SM「虐待式性爱」游戏。一时之间,SM被污名化。本文则说明SM是愉虐而非虐待,意图在主流媒体上将SM的大众通称由「性虐待」改变为「愉虐恋」。好友小林epicure在这之前与之后也持续以实践者身分向大众正名SM为「愉虐恋」。在《岛屿边缘》杂志时期,愉虐恋也被称为「悦虐恋」。